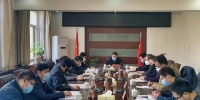日本关东军要塞幸存劳工忆述: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
张玉甫:回忆被骗到海拉尔当劳工的经历——日本关东军要塞幸存劳工忆述之二
奄奄一息的劳工
我是河北滦县人,从祖辈起就房无一间,地无一垅,全凭扛大活混口饭吃。我17岁那年就给本村的一家财主放羊,20岁又扛大活,辛辛苦苦卖力气,所得收入不够还债的。万般无奈,我跑到锦州,在一家日本人的煤矿里当了“煤黑子”。旧社会挖煤那活儿,简直不是人干的。吃的是橡子面,睡在阴暗潮湿的工棚里,受监工的打骂更是家常便饭,经常发生倒塌、爆炸事故,不知夺走了多少矿工的生命。我拼死拼活地干了6个月,除去伙食费所剩无几。正在这时,老爹闹病,我回了家。一登家门,老爹就断了气。以后才知道,父亲久病没钱治,加上好几天没揭开锅盖,活活折磨死了。
等我返回煤矿的时候,日本鬼子一脚把我踢了出来。后来,有人说郑家屯招人,我就望风捕影地又赶到了郑家屯。正是数九寒天,我穿着件露着棉花的薄棉袄,冻得浑身打颤。我挨门逐户地打听:“有用人的吗?”遭到的不是白眼就是一顿臭骂。
一天,我正在郑家屯“蹲街头”,忽然听到有人吵吵嚷嚷地喊道:“招工了!招工了!快来报名!”只见好几个穿着日本服的中国人,手里摇着小旗,上写“招工”二字,边摇边喊。我当时那股高兴劲儿简直没法说,三步并两步地跑到摇小旗的人面前,哀求地说:“先生,求求你,给我报个名吧!”那人问:“你叫什么名字?”“我叫张玉甫。”我又追问一句:“先生,到哪去?做什么活儿?多少工钱?”“叫你们到东山里去开荒种地,每天是三顿白面馒头,一天8小时的活儿,工钱是一元五角。”正在这时,只听摇小旗的人又大声喊道:“自愿报名者,先领15元。”说着拿出厚厚的一沓钞票,在我面前用力地晃着。我立刻就报了名。旁边还有不少中国人也是一手接过钞票,一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。
事情真是一时一变,刚写上自己的名字,马上就身不由己了。我们这些报了名的人,被几个穿着日本军服的人叫到一旁,编上队,马上就送到有人看守的旅馆里,再也不能随便行动了。
第二天一早,我们一批400名劳工,被押到了车站。招工时说乘客车走,到车站一看,等着我们的是四节“大闷罐”,一帮日本兵连骂带赶把我们拥入黑洞洞的车厢,就听“咔嚓”一声,把车门锁上了。我的心“怦怦”地跳了起来,每个人都不解地互相观望着。谁知道什么样的命运等着我们呢?
两天两夜的旅途,把人们折磨得死去活来,每天只给一顿干粮吃,喝不到一口水。第三天深夜,火车突然停了。车门打开,紧接着就听到:“起来,起来,站着队下车!”人们按照次序下了车,车厢外边一片黑,只有地上的白雪反射出一点微弱的光亮。当我们走下车,抬头一望,一排气势汹汹的日本兵,早已在等待着我们。他们一个个手持大枪,枪上的刺刀寒光耀眼,真叫人胆战心惊。点了名,早已准备好的十几辆军用大卡车又向我们开来。“上车,上车!”领队的中国狗腿子向我们大声喊叫着。日本兵端着枪,横眉竖目地吵嚷着。我们刚上了车,又听到中国狗腿子喊道:“不准说话,不准东张西望!”话音刚落,十几辆大卡车便飞一般地向荒无人烟的山里驶去。
天亮了,这时才知道我们已被拉到海拉尔的北山上了。山上布满了长排的工棚,再就是蛛网般的铁丝网和星罗棋布的岗楼,别的啥也看不到了。
我们这400人一直在山上等到天亮,一个个冻得像猫咬一样难受。又等了一会儿,一个非常胖的中国狗腿子开始给我们训话,除讲了些要我们好好干、干好早些回家之类的话以外,说:“你们手里的钱和物品可以交给我们保存,等你们挣够了钱回家时,统统还给你们。”在郑家屯他们预发的15块钱,又原封不动地给了他们。
苦难的劳役开始了。在山上干活儿的劳工少说也有两三千人。我们所干的活儿,说起来只有一种,就是修筑军事地洞。劳动的强度简直就无法想象。无论是打洋灰、挖洞子、挑沟,没有一样是轻松的活。3米多深的壕沟,一锹锹把土扔到上边,干上一天,两肩就别想再抬起来。可是在皮鞭和棍棒的威逼下,劳工们不得不咬牙拼命干,偷不得半点懒。饥饿、劳累、疾病、事故以及日本鬼子、监工们的洋刀和皮鞭,随时都会夺去劳工们的生命。
是真的每天只干8小时的活吗?那是骗人的鬼话。什么叫时间?什么叫休息?根本谈不到,每天不见太阳出工,太阳不落不收工,走回工棚常常是摸黑吃饭。
有这样一件事,我永远不会忘记。那是一天下午,天气十分炎热,简直叫人喘不过气来。一个年轻的“苦力”,已经连续打了好几天的洋灰(这活儿最累),这时他直起腰来,用手擦了把汗,喘了口气,正想再干,不料被监工发现了。他气冲冲地走过来,一把夺过他的铁锹,当头就砍,这个可怜的不知姓名的“苦力”晃了几下身子,再也没有爬起来。接着这个杀人不眨眼的监工冲着我们说:“谁要磨洋工,谁就跟他一样。来人!把他拖走。”不大工夫儿,这个监工在另一地方用洋镐把又打死了一个“苦力”。面对这些血淋淋的事实,虽然我们当时敢怒不敢言,可是都看在眼里,记在心里,偷偷抹掉眼里的泪水。可是,那些野兽般的日本鬼子,每当杀害了中国人都会洋洋得意地说:“中国人大大的有,死了几个没关系!”
他们干起活儿来把我们这些“苦力”当牛马,而在生活上,却连牛马也不如。早晚吃的都是高粱米稀粥,午饭是又酸又硬的混合面馒头,不管饱不饱,一律给4个。每天三顿咸盐豆,喝的是生水,许多人都闹肚子,连拉两天就不像人样了。可是还得坚持出工,要不打入到“病号房”就倒霉了。
提起住的简直没法说。一排席棚子足有半里长,对面二层铺,躺下就不能翻身。工棚阴暗、潮湿,得疥疮、寒腿的人不计其数。一个工棚住着400多人,为了看守方便和不易逃跑,只在中间留一个小门,晚上有人大小便时,非等凑够4个人,拿着4个牌子,一起出去,再一起回来,若逃跑了1个那3个人负责。有时不够4个人,就得等,把人憋得满棚乱走。我记得有一次,白天劳累了一天,收工后躺在铺上就睡了,疲乏得竟连小便都没知觉了,尿在凉席上,又漏在下铺。这事被看守知道了,一下子从铺上把我拖下来,随手拾起洋镐把,劈头盖脸就是好几下,打得我鼻口冒血,至今胳膊上还有一个伤疤。这样的事,几乎每天夜里都会发生。
我到北山后没发给一件衣服。比我来得早的“苦力”说,冬天只给他一套麻袋一样的更生衣,这怎么能抵住零下40多度的严寒?无奈,只好把洋灰袋用绳子绑在身上、腿上,那种可怜的模样,简直连“要饭花子”都不如。每年冬天冻死的人,就没法计算了。
打死、病死、饿死的人越来越多,日本鬼子一天比一天看管得更紧了。事情越来越清楚,我们这些“苦力”的命运,不管迟早最后只有一条道:死!但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念头:跑!有机会就跑出这个吃人的阎王殿,跑出这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窟。
几个月的折磨,我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,不久就病倒了。最初是从眼睛开始的,左眼突然发红,渐渐就模糊不清了。想治,可上哪儿去找医生?上哪里去弄药?几天以后左眼就瞎了。日本鬼子一看我瞎了眼,身上又害了病,知道离死不远了,于是发了“善心”,把我打发到病号房去了。
提起病号房真叫人伤心透顶。一个席棚子住着500多病号,痛苦的喊叫和呻吟声,听了真叫人心酸。这些病号都是卧床不起、米汤不入的,只要还能拿动铁锹,谁也不愿到这里来等死。世间竟有这样惨无人道的事情:得了病不但不给治,反倒每天只给一顿高粱米稀汤喝,据说这是日本鬼子怕劳工们泡病号采取的办法。天天都有新病号送进来。每天早晨,看守都要到病号房里去检查一遍,逐个用脚踢几下,发现僵硬的尸体,便命令拖出去,每天至少三四个,多至七八个。把这些病死的人都堆到一个大席棚里,三四天就用卡车拉一次,扔到伊敏河边。每当河水上涨,伊敏河上到处漂浮着这些“苦力”的尸体。我在病号房里除了“养病”以外,还有一个特别的差使:每天往外拖死尸。
我在病号房住了些日子,趁机逃跑的念头就更强了。因为病号棚离工棚较远,看守得也比较松。虽然总想跑,可是心里有点害怕,万一跑不成被抓回来那可怎么办?那还是我到病号房以前的事。一个不知姓名的“苦力”半夜跑了出来,没等他越过铁丝网,日本鬼子便带条狼狗把他抓了回来。第二天我们站队去上工,发现在道旁的电线杆上,五花大绑高吊着一个血肉模糊的“苦力”,身上被剥得光光的,鲜血从身上流到地下。这个有骨气的中国同胞,虽然身遭毒鞭,但一声不吭。我们再也不忍心看下去了,可是恶毒的鬼子,为了杀一儆百,非叫我们看着打不可,并大声地向我们说:“谁要逃跑就和他一个样子……”这个中国人一直被吊打了两三天,晚上蚊子、小咬糊遍了他的全身。一想到这些我心里着实有些胆怯,可是又一想,不跑也没活路,万一跑出去也许还能有条生路。跑!主意就这样打定了。
1936年7月的一天夜里,是我永生难忘的日子。这天深夜,天黑得伸手不见掌。病号们的呻吟声渐渐低了下来。门口的看守在用口琴吹着日本小曲。突然,口琴声停止了。不多时,门口又传来轻微的鼾睡声。“看守睡着了?”我心里猛地一亮,就轻轻地光脚下了地。走近门口一看,看守果然坐在那里抱着枪睡着了。“好机会!”我顾不得多想,小心地拉开门,从看守面前走了过去,随后我就使出全身力气撒腿跑了起来。
我分不清东南西北,也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跑对,只是往黑暗的地方跑。可是刚跑了不远,一道铁丝网就横在我的面前。我过去只听说这里有高压电网,现在遇到的是不是呢?当时真是吓糊涂了,用手一摸没电,于是我就用手扒个空子,用力钻了过去。衣裳被撕破了,手上流着鲜血,我还是一个劲儿地往前跑。又跑了几十米,又是一道铁丝网,接连一口气爬过了7道铁丝网,最后还有一道深沟。这时,我全身没有一点好地方了。我漫山遍野地跑着,遇到山坡就滚下去,遇到深沟就爬过去。也不知道跑了多远,一直跑到天亮,才知道我已经跑到西山松树林里了。
在西山松树林里,我整整躲藏了两天两夜。白天我不敢露面,藏在草棵子里,晚上出来采点野菜充饥。两天两夜真比两年还难熬啊!第三天早上,我已经饿得昏昏沉沉了,想找点野菜吃也爬不动了,我心里暗说:“张玉甫呀!虎口狼窝你都闯过来了,难道今天就活活饿死在荒山上吗?”我不禁落下了眼泪。
正在这时,忽然听到马车的声响,我赶忙又藏起来,心想这回可算完了。走近一看,原来是几个中国人,谈论着打羊草的事儿,我这才放了心。我壮了胆子向他们走过去。他们见了我吓了一跳,因为我当时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呀!这几个中国人给了我几张大饼吃,救了我一条命,又指给我到街里的安全去路。我谢了他们,一直向海拉尔街里走去。
[责任编辑 哈丽琴 ]
| 欢迎关注: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平台——扫描上图二维码或搜索内蒙古日报(或直接输入neimengguribao)关注内蒙古日报官方微信。转载请注明出处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