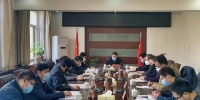【身边好人】蒙古族女教师格日勒:30年,默默守候着一方净土
原标题:蒙古族女教师格日勒的坚守心路 30年,默默守候着一方净土
清水河县五良太小学,蒙古族女教师格日勒只身一人坚守在她的三尺讲台,台下只有两名学生。从教30年,有的学生已经年过四十,随着生源减少,学校其他老师陆续调走,她是校长,原本也有调到其他学校的机会,但她没有离开,这里有需要教育的孩子。她说,“只要有一名孩子还在上学,就会坚守在这所小学。”
12月4日上午,格日勒老师坐在那架陪伴了她数十年的脚踏风琴旁边,打开音乐书,开始弹奏演唱《上学路上》。学生刘佳慧站在她身边,跟着她一遍又一遍地唱。“太阳当空照,花儿对我笑……”,悠扬的歌声在空荡荡的校园内回荡。这样的情形只是格日勒老师在五良太小学坚守的一个聚焦点,从30年前在土坯房中任教到担任校长再到现在的默默坚守,格日勒从未离开五良太小学。
从教:30年坚守在一所学校
格日勒仍然记得当年刚到五良太小学任教时的情形。1984年,格日勒从清水河县的培训学校毕业,回到五良太村,当年的学校还在山坡上的土坯房中,三年后搬到平坦处现在的校址。格日勒说,“我1981年高中毕业,后来到清水河县参加培训学习,当年在清水河县,有蒙古族但是不会说蒙古语,我就是送去学习蒙语,毕业后分配回原籍,当时我21岁。”
刚分配回农村的时候,格日勒教数学,随着老师逐渐调走,课程增多,她开始兼任音乐老师。格日勒的父亲是呼市玉泉区百什户人,后来到清水河县五良太工作。“我出生在这里,在这里工作三十年,十里八乡都有我的学生,只要有一名孩子还在上学,就会坚守在这所小学。”格日勒说。
随着当时撤乡并镇和大量农民外出打工,农村生源减少,五良太小学和其他农村学校一样,学生锐减,老师也逐渐开始流动。后来由于没有英语老师,上了小学三年级以后,学生开始到县里或者到附近的红河镇小学读书。2011年,格日勒成为五良太小学校长,当时还有五六名老师,六七个学生。格日勒坦言,“由于学生数量减少,有的老师担心自己的饭碗,就寻找出路,调到其他学校,但我看到还有学生,就留了下来。”
相处:像亲人更像长辈
依然在五良太小学上学的两名孩子和格日勒的相处更多的像是亲人,感觉不到老师的威严,更多的是长辈的关怀。谈话间,格日勒一直站在刘佳慧的身边,时不时地摸摸刘佳慧的辫子。
12月4日,五良太小学的教室里只坐着刘佳慧,另一名上幼儿园的小男孩跟随奶奶去天津看望婶子。格日勒介绍,小男孩的父亲和爷爷奶奶在五良太乡里开饭馆,母亲是外地人,身体不太利索,孩子又特别淘气,没人照顾,4岁时就送到了五良太小学。就这样,格日勒扮演着老师和保姆的双重角色,给孩子启蒙教育,还得照顾孩子上厕所。
刘佳慧之前在呼市上学,有点儿智障,在呼市上学时经常受到同学们欺负,父母决定将她送回五良太小学上学。当时刘佳慧母亲和格日勒说,有几年级,就让刘佳慧跟着几年级上。
刘佳慧在呼市上到三年级,但回到五良太小学时,格日勒发现她学得东西也就是一年级的水平,格日勒征求了父母意见后,带领刘佳慧从一年级学起。“孩子主要是记性不好,教给的东西很快就忘了,我刚开始教了加减法,她母亲打电话说不要教乘法了,教也很难教会,但我感觉孩子以后还能用得着乘法,我就教,现在基本上教会了乘法,下一步学习万以内数字的读法。”格日勒介绍。经过一年多学习,问起刘佳慧还想不想回呼市上学时,刘佳慧就说,不想回去,在呼市上学同学们打她。
对于刘佳慧的教育,也无法跟上教学大纲的规定,只能是尽量的让刘佳慧认识更多的字。虽然只有两个孩子,格日勒开设的课程没有落下,黑板上整整齐齐地写着生字,她经常带着刘佳慧一遍一遍地朗读,她还经常弹奏那架老式的脚踏风琴,带两个孩子反复唱歌,一册音乐书上,已经学到了《上学路上》。两个孩子在校园内玩耍时,她有时就站在一边看着,有时带着两个孩子玩老鹰捉小鸡和踢毽子等游戏。
在格日勒的心中,所有付出都值得,她说清水河县教育局的领导在每年开学时都会到五良太小学看看她,询问她学校里教学所需。“说是过几天县里的主要领导还来看我。”说到此处,格日勒露出自豪的笑容。
刘佳慧虽然沉默寡言,但问到格日勒老师对她好不好时,悄悄地告诉记者,“对我好,还给我买文具。”刘佳慧课桌上的橡皮泥都是格日勒老师用她的工资为两个孩子买的,有时候发放的作业本不够写了,格日勒就为两个孩子买些作业本。
坚守:不打算离开这片土地
格日勒的一儿一女分别在乌海和包头工作,在她一人坚守在五良太小学的这些年头里,丈夫是她最好的帮手。
五良太小学到了冬天生火炉取暖,每次拉来煤,格日勒只能让老公帮忙,老公开着三轮车,一趟一趟地从路边将煤运到学校库房。今年,学校里安装了自来水,但是有时候因为屋子冷将自来水管冻住,格日勒就从家里提水,在火炉上烧开,给两个孩子喝。
格日勒仍然和当年学生多的时候一样,每天写教案,一段时间还会写汇报材料,一个写有“群众路线学习笔记”的本子上,端正地写着“格日勒”三个字,里面全是坚守在五良太小学的感受和学习心得。
仍然留在农村的学生,大多家庭比较困难,或者是父母不好好照顾孩子。格日勒记得,2013年冬天,学校里只剩下刘佳慧和附近村子里一个名叫吴梦春(音)的同学。吴梦春每天需要走1公里的路上学,格日勒发现,吴梦春每天到校时不戴帽子,她给家长打电话,家长说出门的时候戴着帽子。格日勒翻开吴梦春的书包,发现书包里装着一个三两岁小孩子戴的尖顶毛线帽子。格日勒推测,可能是吴梦春感觉那顶帽子不好看,在出门的时候怕父母骂戴上帽子,到了半路又将帽子装进书包。看到孩子可怜,格日勒有一次到清水河县城开会时,给吴梦春和刘佳慧每人买了一顶帽子、一副手套、一条围脖。
格日勒说,教书这么多年,好多事情都不记得了,这些都是小事。
记者了解到,那名上幼儿园的小男孩再过两年上一年级时,父母就会将他送到县里上学,到时候,学校里可能只剩下刘佳慧。刘佳慧今年16岁,可能再过几年,也要离开学校。说到这些,格日勒眼角发红,有些伤感,她说,“等到这几个孩子离开这里,我也快退休了,我不打算离开这片土地,我依恋这里的一山一水,喜欢这里的人。”(首席记者 邢占国)
[责任编辑 李珍 ]