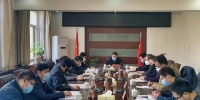足斤足两木杆秤
足斤足两木杆秤
李连红和他的作品
用圆规定刻度
制作秤盘
讲解钉秤原理
自制的商标
木钻打孔
能工巧匠李连红
郭文祥向记者推荐的能人是他的堂叔郭双红老人。郭双红75岁了,身体硬朗,但是听力不好,无法进行采访。随后,老人的儿子郭福珍又向记者推荐了他的叔叔李连红。
钉木杆秤不是一个简单活儿,一杆木杆秤顺利完成,要用到木工、白铁皮工、铆工、焊工、铸铁工等一些工艺。如果无法做到触类旁通,根本不可能做出让老乡满意的产品。
在手工技艺这方面李连红的悟性很高,看上一会儿就能看出门道,很多手艺都是偷学的。他说:“任何一门手艺都有其奥妙,掌握了其中的关键环节,也就掌握了这门手艺的技巧。”
钉木杆秤这门手艺是李连红20多岁的时候在街上学来的。他说:“那年,两个南方人在我老家街上钉秤,边钉边卖,我就站在一旁看。看了一上午,我看明白了。回来后我也学着钉,不过我钉的第一杆4斤的秤钉成5斤的了。”
钉错了,李连红就找来标准秤对照琢磨,很快他就知道什么地方出了问题。钉秤那些年,李连红也修秤。他也见过那种动了手脚的秤。他说:“那种秤的秤杆可以收缩。捣鬼的人都心虚,那人一面让我修一面还抓着秤杆不松手……我特烦这种人,我说‘松开,我做秤多少年,这点儿名堂还看不出?’”
上百道工序繁杂
近年,由于身体的缘故,李连红不再钉木杆秤,“破四旧时,我受到了整治。但是我没有把这些工具丢掉,这些工具是我自己研究制作的,有感情啊!”
李连红制作木杆秤的工具有平刨、圆刨、圆规、手工木钻、锉刀、大铁剪、铬铁等,很多工具虽然搁置了多年,但仍不影响使用。
“我有白铁焊的基础,所以学习制作木杆秤并不难。”李连红说,“我学做木杆秤时,呼和浩特市已经有专门制作度量衡的厂子。当然我用的一些材料可没有大厂子里的整齐,不过我做出来的秤绝对结实耐用,丝毫不差。”
李连红已经记不得几十年来他到底做了多少杆秤。“以前做的秤都卖了,家里只留下3杆秤平时使用。”李连红拿出一根木杆对记者说:“这是一根还没有钉秤星的秤杆,秤盘要用白铁皮来砸成,秤砣要去铸铁厂定做。”
用圆规确定秤杆上秤星间的距离,是李连红自己悟出的。“圆规标出来的刻度更精确。秤星多是用铜丝、铝丝或者银丝做成,镶秤星时需要先用手工木钻在标好的刻度上钻眼,再用金属丝嵌入小孔内,再掐断,敲入,锉平。做秤星是一个考验眼神和手准的活儿。”李连红架上高度的老花镜,为记者演示镶秤星的过程。他告诉记者,传统手工制秤十分繁杂,有100多道工序,要经过选料、刨圆、套铜套、配砣、装钩、分级、打眼、磨光、校正等。
老秤自古讲公平
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法制计量的文明古国,无论从古代计量精度上看,还是从计量单位和计量管理体制上看,都是举世无双的。公元前221年,秦始皇统一了度量衡。东汉初年,木杆秤应运而生,到了唐代,秤上又多了钱、分、厘等单位,七钱为一两,七分为一钱。木杆秤沿用十六两为一斤的规矩,延续了1000多年。解放后又改成了十两进制。在上世纪80年代以后秤就和国际接轨,以千克为标准。
木杆秤制作工艺精度要求高,具有一定的保存价值。木杆秤有两种,一种是十六两一斤的叫做老秤,一种是十两一斤的叫做新秤。老秤的一两是三十一克多一点,人们习惯称作小两,新秤的一两是五十克,人们则称作大两。中国的老秤,十六两为一斤,在秤杆上有十六个刻度,每个刻度代表一两,每一两都用一颗星来表示。秤杆上的七颗星是代表北斗星,六颗星代表南斗星,除这十三颗星外还有三颗星,分别代表福、禄、寿三星。如果商人给顾客称量货物少给一两,则缺“福”;少给二两,则表示既缺“福”还缺“禄”;少给三两,则“福”“禄”“寿”俱缺。
秤杆分木杆秤和金属杆秤两种。金属杆秤晚于木杆秤出现。在杆秤上有颗大星,当秤砣挂在大星这一位置,秤盘又无任何东西时,提起提绳,则两边重量相等,秤杆平衡。这颗大星叫定盘星。定盘星,被赋予了公平、公正、公开之意。
秤杆是六道子木
对于木杆秤而言,秤杆的材料也相当关键。“大厂子钉秤杆用的是红木,我没有红木,就用当地产的木材。”李连红说,“在几十年前的大青山上,生长着一种灌木,叫六道子木。六道子木是一种枝干表面有六道竖棱的灌木,这种灌木粗细匀称,没有大的枝杈,坚韧结实,越磨越亮,可以做木耙、木叉等农具,放羊的用它做鞭杆。六道子木一般长在高山密林中。”
生长在城里的人大多不知道也没有听说过六道子木。据信佛的人说,六道子木是做念珠的上选之料。还有就是习练太极者,要用六道子木做太极鞭杆。
李连红说:“早些年,六道子木在土产门市就有出售,老乡把一根根六道子木从山上选割下来,用火烘干后卖给土产门市,一根不过几毛钱。”
李连红把从土产门市买回的六道子木放在家里的水缸里泡上一宿,第二天,一根根浸过水的六道子木变得很直。然后李连红再用圆刨把整根的六道子木去皮、刨圆,秤杆就取材于刨好的六道子木木心。
六道子木木心是白黄色,为了与秤星的颜色形成反差,李连红用红色印泥把做好的秤杆进行染色。染好的秤杆久不褪色,愈磨愈亮。
磅秤的出现,让杆秤退出了生产领域。后来,电子秤的出现又让杆秤在生活中渐渐销声匿迹。当杆秤成为收藏品时,李连红失落的心情可想而知……
征集线索
民间的才是鲜活的。你还记得吗?那些曾经鲜活在我们身边的老行当,还有那些曾经生活在我们身边的老艺人。
“磨剪子嘞……”当一声悠扬的乡音响起,无论在哪里,总能唤起心底的一片温暖……高一声低一声的吆喝,走街串巷的背影,总让人无法忘怀——做鞋的、修脚的、箍桶的、补锅的、织麻的、编筐的……当年,有着生存压力的他们,只是为了简单的生活。如今,回访曾经的他们,经典会令人感动。时代在变迁,社会在发展,曾经的许多,淡出了我们的生活,却淡不出我们的记忆。如果你身怀技艺,如果有你熟知的老行当,请拨打手机13948197147与本报记者联系,我们会用笔和镜头,记录下一个个瞬间,留作永恒。
铸铁秤砣
钉木杆秤这门手艺,在南方多有传承,在内蒙古农村少有人掌握。10月23日,读者郭文祥推荐这一手艺时,记者多少有些意外。几经辗转,家住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小黑河镇的李连红浮出水面。
67岁的李连红不钉木杆秤已经有些年月。保存完好的钉秤工具,承载着他以往的辉煌,“年轻时,在材料配齐的情况下,我3个小时就能钉出5杆秤,现在老了,手抖,眼神也不好,做不成了。”文·摄影/首席记者辛 一
[责任编辑 魏佩 ]